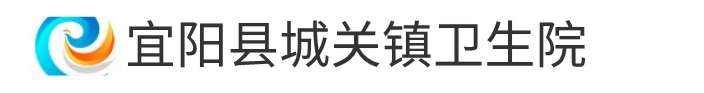常武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近期发布了《关于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国家卫计委与国家中医药局将于今年8月至明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对医疗机构的依法执业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在此过程中,二级和三级医院是否出现科室出租或承包的情况,将成为检查的重点之一。
长期以来,部分公立医院通过签署合约或协议,将院内的特定科室或数个科室委托给特定的租赁或承包方。这些被委托的科室以公立医院科室的名义展开运营,医院则从中收取相应的承包费用,亦或是与承包方按比例分享收益。此类科室外包导致的结果是,公立医院与承租方之间仅存在单一的利益纽带,医院仅着眼于收取租金或收益分成,对外包科室的业务监管有所松懈;承租方为了迅速收回投资,必定会忽视公立医院应有的公益性质,将从患者身上获取利润视为首要任务医院科室外包,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唯一追求。
在利益驱使不断加大的背景下,科室外包现象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虚假广告的泛滥、诱导性治疗的盛行、过度医疗的频繁发生,乃至对患者进行恶意欺诈等一系列违规违法行为的出现。“魏则西事件”之所以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揭示了公立医院科室外包所引发的种种乱象,严重损害了患者的合法权益。
公立医院若选择将科室外包,收取承包金或进行收益分成,不仅能够降低科室的经费及人力需求,减少运营管理费用,而且还能带来可观的收益,这无疑是一项非常划算的交易。科室承包者不仅能够以公立医院的名义对外宣传,利用公立医院长期形成的品牌形象、影响力和公信力资源,更可以自行构建医疗服务体系,绕过常规的医疗监管,从而自如地实施虚假宣传、诱导性治疗等违规违法行为,竭尽全力榨取患者口袋中的每一分钱。
原本,按照常规的法律视角,公立医院作为“房东”,对外包科室仅应担负有限的责任,而外包科室作为“房客”,则需对其行为负全责。然而,鉴于医疗机构的特殊性质和医疗行为的特性,公立医院与外包科室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于普通的“房东”与“租客”。这种责任关系存在诸多模糊地带,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往往难以明确界定和充分追责,导致患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救济和保障。
鉴于科室外包可能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和负面影响,我国中央及卫生监管部门持续发布禁令,严格禁止公立医院进行科室外包。例如,在2000年,原卫生部、财政部等四个部门共同发布文件,明确指出由政府出资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合资或合作,设立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盈利性科室、病区或项目。2004年,我国卫生部及监察部等相关部门对一家制药集团涉嫌在多所医院中承包科室的行为进行了调查。此后,卫生部迅速发布了一项紧急通告,强调各地医疗机构不得将科室进行出租或承包,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进入去年六月医院科室外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社会办医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再次明确规定,承包和出租科室的行为依然被明确界定为政策所禁止的范畴。今年五月五日,正值“魏则西事件”不断升温之时,我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紧急召开了一场电视电话会议,强调医疗机构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执行合法执业规范,并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科室出租或变相出租行为。
这些接连发布的文件和反复强调的规定,为何仍难以有效遏制公立医院科室外包出租的现象?一方面,部分公立医院及其科室承包方普遍存在强烈的盈利欲望;另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不足,积极性不高,与前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些地方和部门的监管执法人员,与公立医院及科室的承包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关系。他们对公立医院违规外包科室的情况了如指掌,却常常故意或无意地采取放任态度。由于监管执法不力,追责惩处不够严厉,导致那些禁止公立医院科室外包的文件和规定实际上失去了效力。如此下去,不出问题才真是奇怪呢。
此外,众多民营医疗机构对公立医院特定科室的承包表现出浓厚兴趣,这反映出社会对于相关医疗服务有着真实的需求。这些需求中,部分涉及基础医疗保健领域,理应由政府设立的非盈利性公立医院来承担;而另一部分则属于特殊或高端医疗服务领域,则可由非公益性质的私营医疗机构来提供。但无论如何,绝不应允许私营医疗机构以类似“四不像”的模式承包公立医院的科室。
公立医院科室外包问题已成为一大难题,亟需采取强力措施和深入改革来全面解决。为此,国家卫计委与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专门的监督检查活动。此举旨在全面掌握全国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评估这一严重问题的治疗进展与效果。专项监督检查需严格执行现行法规,对违规违法行为实施严厉查处与惩罚;从战略角度出发,需增加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资金支持,积极推动并扶持社会力量兴办医疗机构,共同扩大公立与民营医院的市场份额,有效缓解医疗服务供给短缺的现状,从而彻底根除公立医院科室外包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