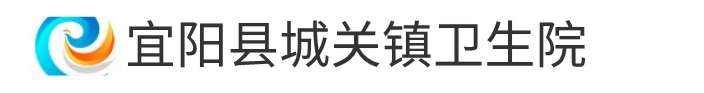在当代神经科学领域,阿尔茨海默病(AD)被形容为一种“边界不清的疾病”:我们清楚了解其结局,但对于其初始阶段却始终难以明确划分。
尽管Aβ斑块和Tau缠结被认为是其典型的特征,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这些所谓的“特征”可能仅仅是疾病晚期的表现,而非疾病的根本原因。或许,真正的病源深藏在更为早期、更为广泛、也更为复杂的生物变化之中。
2025年,《Trends in Neurosciences》(影响因子:15.1)上的一篇文章并非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见解,而是一个长久以来被遗忘的质疑——若阿尔茨海默病(AD)并非由衰老或基因因素导致,而是由感染引起的慢性炎症所致,我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证实呢?
我们是否依旧沉浸在“寻找病源”的单一思维模式中?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迎接那些病因并非单一、病程可能呈现出“网络式演变”特征的疾病模式的准备?
一、为什么“感染假说”曾长期被边缘化?
并非无人提及——自1990年代起,便有研究指出HSV-1病毒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脑组织样本中存在显著增加的情况。
但这一假说始终未能进入主流原因有三:
1、它打破了“神经退化 = 基因决定论”的稳定叙事结构;
2、感染不容易建立因果关系,常常被误解为“相关噪声”;
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过分集中在Aβ和Tau等蛋白质异常的机制上,却忽略了从免疫学和微生物学的角度进行探讨。
然而,这恰恰是本篇综述的核心所在——对病因的定义进行重新审视,对“可证伪性”这一标准进行深入思考。
二、作者提出了怎样的验证路径?
他们并未仅仅提出“病毒引发阿尔茨海默病”这一观点,而是深入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性的、充满哲学思考的问题框架。
若慢性感染成为阿尔茨海默病的诱因,那么在阿尔茨海默病的脑部组织中,我们是否应当频繁发现病原体的存在?
2、若是真正的因果,应当能在动物模型中重建病理过程?
3、进一步,若清除病原体,是否能减缓或逆转病程?
如果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机制,那么在人群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应当观察到某种趋势性的、与剂量相关的反应关系。
换言之,这不仅仅关乎生物医学领域的验证难题,更涉及到逻辑哲学层面的“归因理论”:何为真正的病因?我们又如何能够称之为“证实”呢?
三、“Aβ是杀手”还是“最后的防线”?重新定义病理标志物
作者进一步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β-淀粉样蛋白(Aβ)或许扮演着“抗菌肽”的角色,这可能是大脑对抗外来入侵者所采取的一种防御策略。
换句话说,Aβ之所以存在,或许并非出于它想要对我们造成伤害的意图,而是它在试图保护我们——尽管这样的保护代价高昂。
这一观点极具理论洞察力,迫使我们对过去数十年所遵循的以“清除Aβ”为核心的治疗策略进行深刻的反思,质疑其是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或许我们的目标并非彻底消除它,而是深入探究并消除导致其不得不出现的根本——病原体。
四、疾病的真正根源:持续炎症,而非瞬时感染
文章中,科学家们进一步阐释道:尽管感染可能开启了这一过程,但真正导致神经退行性病变的,却是随后发生的慢性神经炎症。
这是一场低强度、持续多年的“免疫内战”:
1、小胶质细胞持续活化;
2、NLRP3炎症小体因病原体代谢物或Aβ持续激活;
脑内持续存在干扰素、IL-1β、TNF-α等炎症因子,且这些因子的水平长时间保持在较高状态。
结果就是:血脑屏障破坏、神经元凋亡、突触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所谓的“神经免疫激活”现象,实际上与肠道菌群、口腔中的微生物,乃至常见病毒的慢性感染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发现使得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不再仅仅局限于大脑疾病范畴,而是将其纳入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系统层级——一个涵盖神经、免疫以及微生物组的综合性系统性疾病模型之中。
五、多种病原体,一种病理机制?
这一现象引人深思:并非单一病原体引发了AD相关的炎症和病理变化,而是由多种“普遍存在却难以根除”的微生物共同作用所致。
作者提到的病原体包括但不限于:
1、疱疹病毒家族(HSV-1、VZV、CMV);
2、口腔菌(P. gingivalis);
3、真菌(C. albicans);
4、螺旋体(如梅毒、莱姆病);
5、甚至是新冠病毒(SARS-CoV-2);
6、HIV病毒与内源性逆转录病毒(ERVs)
7、肠道菌群失衡
这些病原体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即感染后难以彻底根除,往往进入长期潜伏期,并周期性地被激活,进而诱发轻微的炎症反应。
也就是说,AD的成因可能并非单一病原体所致,而是慢性感染作为一种持续的免疫压力,长时间对大脑的稳定状态造成破坏。
从“单一病原体”的概念,到“感染负荷”的考量,从“病原入侵”的过程,到“免疫崩溃”的结果,这些正是AD感染假说与真实生物现象更为贴近的所在。
六、如果成立,会带来什么改变?
若未来大规模研究得以证实“慢性感染是引发阿尔茨海默病的关键因素”这一理论,那么它将对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及临床实践产生三项重大影响:,,,。
1、从蛋白假说到“免疫-微生物”整合模型
AD或许是大脑长期应对慢性微生物入侵的“免疫副产物”;
现有“清除Aβ”策略应转向“识别+阻断病因+调节免疫”。
2、治疗方向打开
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神经药物”,或许可以拓展至包含抗病毒、抗菌、抗炎等多元化组合治疗方案。
已有药物如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s)也正在进入临床试验。
3、筛查和预防方式改变
高危人群或需检测口腔炎症、疱疹载量、肠道微生物群;
长期感染史(如带状疱疹、牙周炎)可能成为AD风险指标。
也许,我们一直在问错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过于偏向于“内向”视角: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脑部神经元、蛋白质的聚集以及遗传上的变异上,似乎一找到那个“异常蛋白”的起源,就能解开所有谜团。
这篇文章让我们意识到,或许我们对“病因”的本质理解存在偏差。一种疾病的产生,并不一定源于体内组织的病变,或许是一场身体与外界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失衡。大脑在持续遭遇外来入侵时,不得不启动免疫防御机制,然而,这种自我保护的行为最终却可能自食其果,导致生物系统的全面崩溃。
Brutkiewicz RR, Cao W, Morgan D, Reis RSD, Suryadevara V, Willette AA, Willette SA, Wyatt-Johnson SK, Duggan MR. 探讨证实慢性感染为阿尔茨海默病病因所需条件的研究。Trends Neurosci. 2025年6月16日出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S0166-2236,卷号25,期号00104-3。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10.1016/j.tins.2025.05.009。已在线发表,PubMed ID:40527696。